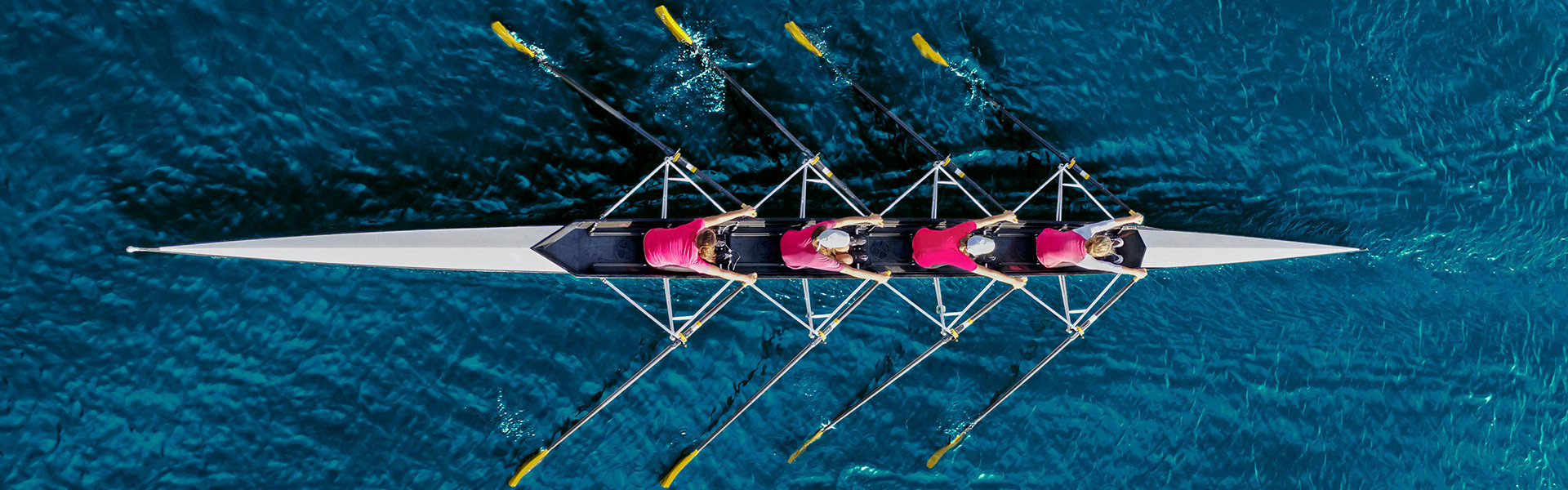英媒:打造未来战斗机的竞赛

一名男子站在“暴风雨”(Tempest)战斗机模型的机翼下——这将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下一代战斗机。 摄影:News Licensing
3月21日,美国前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宣布美国未来战斗机F-47将由航空巨头波音公司建造时赞叹道:“从速度、机动性……到有效载荷,从未有过任何机型能接近它。”这款战机是全球多国绘图板上所谓的“第六代战机”之一。
2022年12月,中国展示了被认为是歼-36的原型机——这是一款具备隐身特性和大型飞翼设计的 imposing 战机。英国、意大利和日本正在联合开发本国的第六代战机(英国暂称“暴风雨”),计划2035年服役。法国、德国和西班牙则希望其“未来空战系统”(FCAS)能在2040年前就绪。这些机型共同勾勒了空战的未来图景。
战斗机通常按年代、功能和先进程度划分代际。第一代战机出现于20世纪40至50年代;如今北约服役的许多机型(如美国普及的F-16)属于第四代,建造于20世纪70至90年代;最新的第五代战机(如F-35和F-22,后者可能是目前全球最领先的现役战斗机)则具备隐身能力、持续超音速飞行能力和先进计算机系统。
与早期机型相比,第六代战机有一个共同特点:体型庞大。F-47的早期图片经过大量模糊和剪辑处理,可能与最终机型差异较大。但歼-36的照片和“暴风雨”模型(如图)显示,这些战机的体型远超第四代的中国歼-20、欧洲“台风”,以及第五代的美国F-35和F-22。这种相似性表明,各国对未来空战有着相似的预判。
各国均预测,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将愈发密集——乌克兰战场上防空系统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知。这要求战机具备更强的隐身能力以避开敌方雷达,而隐身需要光滑的机身表面:炸弹和导弹不能外挂于机翼,必须隐藏在更大的机身内部。
过去40年,“超视距”空战的比例稳步上升——从20世纪70年代的极小比例,增至1990至2002年间的半数以上。此后,空对空导弹的射程不断突破:欧洲“流星”导弹射程200公里,十年前首次测试时堪称技术前沿;如今美国AIM-174B和中国PL-17已能击中400公里外的目标。这意味着战机需要更先进的传感器以远距离探测和攻击目标,还需更强的电子战设备抵御威胁。这些技术需要更大空间来供电,并解决电子设备产生的大量热量。
战机在地面时易受远程导弹攻击,因此需要从更远处的机场起飞,这要求更大的油箱和更低的飞行阻力以提高效率。航空专家比尔·斯威特曼(Bill Sweetman)指出,“暴风雨”和歼-36的巨大机翼正满足了这两点。对美国而言,航程尤为关键,计划在战时将战机分散部署至更远的跑道(如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)。
英国皇家空军负责“暴风雨”作战应用规划的比尔上校(Group Captain Bill,未透露姓氏)近期在“暴风雨团队”播客中表示:“我们讨论的是真正的超远射程。”他称,该战机需具备“单油箱跨大西洋飞行”的能力,而如今的“台风”战机完成同样航程需空中加油三四次。背后原因包括:曾安全部署于前线后方的大型空中加油机,如今日益受到PL-17等新型空对空导弹的威胁;此外,“暴风雨”可绕道飞行,避开俄罗斯防空系统的主要拦截路径。
综合上述需求,新一代战机外形更接近老式轰炸机。斯威特曼将体型庞大、机翼宽大、武器舱深邃的歼-36比作“空中巡洋舰”,其设计更注重航程、隐身和载弹量,而非狗斗机动性。比尔上校强调,“暴风雨”的首要需求是“强大的武器携带能力”,约为最重F-35的两倍。这一设计逻辑清晰:若每架次能投放更多火力,便可减少深入敌方空域的危险飞行次数。曾为英国国防部提供空战设计咨询的迈克·普赖斯(Mike Pryce)总结道:“各国的解决方案趋于一致——保持距离、隐藏行踪、先发制人,避免陷入近身格斗。”
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(Leonardo,与英国BAE系统、日本三菱共同开发“暴风雨”项目)首席执行官罗伯托·钦戈拉尼(Roberto Cingolani)表示,随着战机体型增大,其内部正演变为“会飞的超级计算机”。英国皇家航空学会的蒂姆·罗宾逊(Tim Robinson)介绍,莱昂纳多称“暴风雨”每秒可处理“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数据量”,包括无线电信号、防空雷达电磁辐射等。钦戈拉尼指出,数据可能通过卫星与友军(包括坦克和舰艇)共享,并由“中央人工智能”决策(如攻击目标、武器和时机)。他反驳“这是科幻”的质疑:“不,这是愿景。”
第六代战机是否需要飞行员?特朗普的助手埃隆·马斯克近期嘲讽“仍有傻瓜在造有人驾驶战斗机”。但实际中,多数空军认为人工智能和自主技术尚未成熟到完全取代人类飞行员——英国皇家空军预测,这一突破需等到2040年。《战争地带》(The War Zone)网站的托马斯·纽迪克(Thomas Newdick)指出,F-47的早期图片(尽管未必反映最终设计)显示其“座舱盖较大,为飞行员提供良好视野”。此外,部分任务具有高度敏感性:法国计划用FCAS投放核武器,这类任务可能始终需要人类决策。
不过,主流思路是:第六代战机将成为“空战系统”的核心,由驾驶舱内的人类操控多架无人僚机(美国称“协同作战飞机”,CCA)。钦戈拉尼形容:“这是一个‘会飞的航空母舰’,是在空中机动并自主决策的完整机群。”比尔上校表示,驾驶舱内的人员不应再被称为“飞行员”,而应是“武器系统官”(英国皇家空军术语,指负责管理传感器和武器的人员)。
5月1日,美国空军宣布已启动两款CCA原型机的地面测试,计划今年晚些时候试飞。目前规划显示,每架F-47将配备两架CCA。前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·肯德尔(Frank Kendall)指出,无人机可执行侦察、目标定位或自主攻击任务——均在视距内并处于“严密控制”下。钦戈拉尼(针对“暴风雨”项目)强调,执行这些任务所需的密集计算大多需在有人驾驶的“母舰”上完成,相关数据需实时共享至所有机群,且通信链路必须绝对安全:“我不确定十年内能否实现。”
若技术突破成功,代价将极为高昂。拜登政府时期的肯德尔曾暂停F-47开发,主要原因是其成本预计为F-35的两倍(单架可能高达1.6亿至1.8亿美元),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仅能负担约200架的小规模机群。五角大楼许多人主张,应重点开发CCA以配合现有F-35机群,而非将资金投入可能在中美冲突爆发多年后才能服役的新平台。
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空中力量专家贾斯汀·布朗克(Justin Bronk)表达了类似担忧,他以二战为例:“将国防预算的全部余力投入一个乐观估计也要到2040年才能完全形成战斗力的项目,在我看来就像英国1936年将所有资源投入‘火神’轰炸机(Avro Vulcan)的开发——而该机直到二战结束十年后才问世——却忽视了‘飓风’‘喷火’‘布伦海姆’等实战机型。” ■